因为接受的教育和生活环境影响,自小有了崇仰英雄的情结,也有了“匡扶正义,除暴安良”,“人声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少小价值观。看历史一路走来,仰望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邓世昌、谭嗣同、秋瑾、孙中山、李大钊……一直到佟麟阁、张自忠、赵一曼,同时又知道了“九一八”、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台儿庄战役、平型关大捷等等。青少年时期的我,经常设想自己若处异族暴力入侵之时该当何为?毫无疑问,也一定会“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身为庶民,以生死抗争;幸为军人,决血洒疆场!

草鞋兵(重点在脚下)
二十年前,作家邓贤的《大国之魂》,让我对滇缅抗战从以前的一知半解进而有了基本上全景式的了解。三年前,齐赤军、梁茂林先生的《贵州草鞋兵》让我知道了从淞沪抗战到滇缅边陲,十四年抗战,时时处处激荡着贵州部队的钢铁洪流,喷涌着贵州儿女的滚烫热血。
手执钢枪,背负棉毯、雨伞或斗笠,脚穿草鞋,是上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南方军队战士的普通形象,特别是黔、桂、川、滇等省更为普遍。据梁茂林先生对史料的研究和介绍,当时贵州军队士兵每月只有伙食费2元,另有3毛草鞋钱,许多士兵自己编草鞋,把草鞋钱等节约下来贴补家用。“草鞋兵”装备简陋、英勇抗战的身影,在若干历史老照片里,如在章东磐先生主编、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抗战影像集《国家记忆》里比比皆是,足可印证。那种种艰苦的真实,让人震撼!
有幸,2010年开始,一个偶然的机会,多年宿愿得以初偿。两年多来,我利用工作空余和节假日的时间,或与志愿者作伴,或单人独骑,或携妻带儿同行,循着一些隐隐约约的线索,近百次寻访,行程上万里,风餐露宿,日晒雨淋,走过了云南、贵州以及江西、湖南、广东的很多地方,找到了几十位活着的抗战“草鞋兵”老兵,也听说了更多的一个个形象鲜活经历感人但已先后远行(辞世)的抗战老兵,他们多是贵州人或战后生活在贵州。
发生在上个世纪1931到1945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已经过去70多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活着的抗战老兵,并不是什么传统意义上所崇拜的“英雄”,他们都是普通人,是小人物,是“幸存者”,是战争历史过后长期被忽视的“沉默者”。他们年龄最小的80多岁,大的已过百岁之寿,垂垂老矣。几十年来,他们或居长街小巷,或留穷乡僻壤,各有酸甜苦辣,几近悄无声息,淡然度日,又陆续辞世。直到上世纪80年代,特别是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年以后,他们才逐渐得到公众和社会一定的关注。
斗转星移,自然规律;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老兵们真是老了,但说起青年时期为民族生存的奋战,我们仍然感受到他们在民族和家国危难之时昂然的气节和沸腾的热血:
或跪辞父母,拥别妻儿,报名参战;或投笔从戎,走出校园,奔向战场;或被抓壮丁,始而逃避被动,战时义无返顾;或新婚燕尔,抛却花前月下,携手共赴国难。
或着短军裤、麻草鞋,饥寒交迫顶风冒雪千里行,勒紧腰带举刀擎枪入敌阵;或连战经月,蓬头垢面,衣装鞋袜沾血带肉脱不下,枪不离手,马不卸鞍战犹酣。
—或炮火连天,尸山血海,无长官,无友邻,人自为战,兄弟伙报团就是不后退;或转移不及联系断,弹尽粮绝,退进深山密林,与豺狼虫蚍为伴,以山泉草根为食就是不投降。

在编制草鞋
上百次的寻访,在边远村寨的茅屋里,在曲折小巷的陋室中,灯前月下,床畔炉旁,聆听着老兵们断断续续的回忆。这些带着乡音的平凡话语,展现着真实的历史细节,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华民族全民抗战史:
1942年,离家几千里来到这边(注:云南),一路就是坐车、走路、打仗。我也不记得打了多少仗?我不该死啊,那些弟兄,该死的,一接火(注:开战)就去球(死)了,不该死的,怎样打都不死。我受过三次伤,第三次,“咣当”一声,头上挨了一枪,感觉钢盔在头上转了几圈,醒过来,没死,接着打!(贵州惠水籍老兵陈金刘)
我是机枪手,打比利时机枪。那时十六七岁,个子高。民国33年,过云南高黎贡山,边打边走,山高啊,难爬,下雨又下雪,冷啊,死了多少人。天上还有飞机轰炸,路边的死人一摞(堆)一摞的,冷死的多,也有打死的。我冷得受不了,发脾气,跳起脚骂了连长一顿,后来看没办法,副团长给了我一床旧毛毯顶着,算是没冷死。打腾冲,日本人的炮火厉害,人也厉害,我们打了好久,打进去,又被打出来,又打进去。死的人多了,到处都是,最后终于打进去了。我做的工事好,与别人的不一样,我做的拐个弯,飞机来了也炸不着。我用机枪打过飞机。(贵州普定籍老兵黄良益)—我是迫击炮瞄准手,在印度训练,现在也记得怎样测距离、瞄准。后来就往缅甸、云南打。印象深的是打缅甸孟拱,仗打得凶了。一炮过去,打掉七八个,十多个。那一仗,我们这个部队打死1000多日本人。我们连长死了排长也死了,副排长是为掩护我死的,他人好啊,死得惨啊。几十年,我一提起就难过。后来让我当副排长,我说文化低,当不了。(贵州水城籍老兵丁西伍)
在广西打仗,日本人的炮火好凶。我趴在战壕里,浅了,背包露在外面,一阵炮火打来,背包炸飞了,我没事。后来喊撤退,连长,排长都找不到了,日本人围上来了,有人说,跑吧。我说,往哪点跑?跑得脱不?跑不脱。跑不脱就打吧。又打死好多人,日本人退了,我们才出来。(贵州清镇籍老兵陈自华)
打松山,打了好久打不上去。团长叫集合,叫举手,组织敢死队。我十五六岁,看别人举手我也举手,排长从后边踢我一脚,说:你这个娃娃举哪样手嘛?可也不敢放下来了。因为我是卫生兵,没枪,后来发我几颗手榴弹,就叫跟在后边冲,负责拖伤员,拖死人。有人倒下来,先摸摸有气没有,有气的先拖,没气的后拖,我一天要拖几十个。拖了一个多月,一身都是血,没有衣服换,衣服烂得一条条的,全让血糊住了,也脱不下来了。拖下来的死人,就一堆一堆地堆在那里。(贵州遵义老兵李文德)
1941年,我和丈夫刚结婚不久,我二十二岁,随丈夫在贵阳报名参了军,200师,师长戴安澜。参军前我是师范学校毕业,做教师教书,丈夫是政府机关的科员。参军后丈夫是政治部的中校,我是宣传队的少尉。1942年随部队到缅甸,参加同古战役,打了十多天,伤兵越来越多。上级叫准备撤退,政治部和医院先撤,有伤员,有女兵。我们撤到曼德勒,转乘火车,出站不远,被破坏,火车从中间脱了钩,倒退冲到车站里,爆炸,日本人也进城了。我和丈夫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衣服全烂了,扒了死人的衣服穿上,往深山里跑去。后来遇到十来个打散的兵,一起走。一天晚上宿营在一个山顶的破庙里,日本人半夜摸进来,穿军装的都被杀害了,我们穿的是便衣,没死。日本人用刺刀逼着我们把战友的尸体扔到悬崖下去,我们含着泪一边拖一边在心里请求牺牲的战友原谅。后来日本人又逼着我们拾柴烧饭,我们从庙旁一个悬崖的石缝里逃了出来,在深山里也不知走了多少天,受的苦不说了,我的头发全掉光了,好不容易走到腾冲附近山里,有老百姓给了一碗煮熟的豌豆,那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老百姓又悄悄把我们送过怒江,搭上了往后方送伤员的汽车,后来在医院住了半年。日本人无恶不作,我恨死了他们。(贵州贵阳籍老兵,女,施仲珍)
互联网上的数据,全国现有健在抗战老兵已只有几万人。“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慢慢凋零”[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老兵们正在悄然隐去。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及慈善团体在关注老兵,更致力于寻找老兵,慰问老兵,帮助老兵。有些老兵晚年生活贫寒,疾病缠身,孤独无助,志愿者及慈善团体资助他们看病,修房,补贴他们的生活,定期不定期组织慰问,帮助老兵寻找亲人团聚或回家乡了却心愿,竭尽微薄之力,努力让老兵们感受一些温暖、荣誉和尊严。老兵们当年为国家和民族生存浴血奋战,志愿者们作为后人只想努力给予他们一点回报和感恩。但是,努力每每伴随着遗憾,太晚了,来不及了!老兵们年龄都太大了,太老了,正在加快离去。

送军用物资的草鞋兵
2010年冬天,我与志愿者们据一条偶然得到的线索,一路走一路问,终于在黔北边远山区里找到了参加过淞沪抗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等战役,多次受伤,身带残疾的贵州遵义籍92岁老兵舒仕忠。他与唯一的60多岁舍家来陪伴他18年的女儿住在一间四处透风见亮,晴不遮阳,雨不挡水的破房子里,疾病加战伤残疾,行动已很困难,情景凄凉。现场二十多个志愿者,无论少长,人人热泪长流,有的放声大哭。志愿者们捐款捐物、请医购药、筹备建房……地方基层政府也伸出援手,历经数月,老人家病情好转,饮食渐增,还高高兴兴住进了为他原地修建并配好家具、电视的小小一间新房,同时接受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派来专人的采访,但住进新房仅仅12天,老人家走了……很多志愿者因此几天不能入睡。他们想,老人家是找他的战友们去了,他在这边是不是感觉有些孤独?在那些曾经是炮火连天战场的地方,他有很多战友,有很多……。
淞沪抗战纪念馆采访组的同志们告诉志愿者,他们每次出来采访,都有顾虑,经常是人还未回到上海,路途上就接到电话:老人家走了。近几年来,我与志愿者们,找到并看望、帮助的老兵有70余人,但是每年几次有时甚至是连续几个月,都接到老兵逝去的消息。志愿者们每每伤心自责:我们关注太晚了。面对虽然健在但日渐减少,渐行渐远的抗战老兵群体,还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或没有找到!?要快啊。那一天,一定要让老兵们少带走一些遗憾,多带走一点温暖,一定要让他们带着荣誉和尊严,去天国集合,去拥抱那些早逝的战友,去共同感受家园和后人永远的尊敬和怀念!
向您致敬!渐行渐远的抗战“草鞋兵”!(作者:杨崇岭)
(责任编辑:刘涵)
-
无相关信息



 梅花如雪芳香不染——从贵州走出的..
梅花如雪芳香不染——从贵州走出的.. 震惊中外的“东华门事件”——贵州..
震惊中外的“东华门事件”——贵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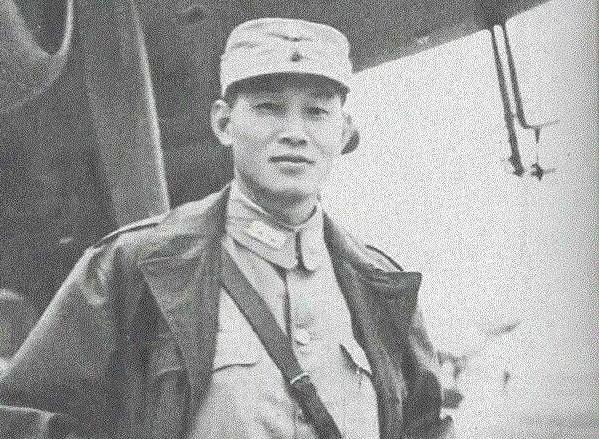 抗战名将孙立人:曾击毙日军3万3千余..
抗战名将孙立人:曾击毙日军3万3千余.. 民主先锋——孙中山亲定他代表贵州..
民主先锋——孙中山亲定他代表贵州.. 中国汉人王朝末代皇帝陵墓在贵州发..
中国汉人王朝末代皇帝陵墓在贵州发.. 人文贵州,于斯为盛——中华民国“二..
人文贵州,于斯为盛——中华民国“二..





